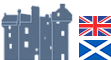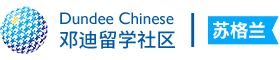英国邓迪留学社区
Dundee Chinese
欧洲为何落后于美国?
titan(2008/1/13 1:29:46) 点击:68291 回复:0 IP:60.* * *
titan(2008/1/13 1:29:46) 点击:68291 回复:0 IP:60.* * *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拉尔夫•阿特金斯(Ralph Atkins)
2008年1月10日 星期四

埃
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是一位生性好斗、年过七旬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以其对欧洲发展前景犀利的嘲讽而闻名。作为这样一位人物,他选择在一家纽约餐厅用午餐显得较为保守。Isabella's餐厅地处上西区一座七层高、带有金属火灾逃生口的红砖建筑底层,餐厅里满是享用着美式食品的父母和孩子。明亮的餐厅可以俯瞰对面的学校。
这位2006年诺贝尔(Nobel)经济学奖得主来得非常准时。菲尔普斯生于1933年,又高又瘦,笑得很灿烂。他穿着一件浅绿色格子图案的夏装夹克,打了一条棕色领带;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最近在世界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刚从圣保罗回来。他看着菜单说:“重新和我的祖国建立联系挺不错。”
随着他愉快地接受了女服务生的建议,先来一杯加利福尼亚白葡萄酒,我的希望油然而生:这将是一顿快乐的午餐,而不是一场智力方面的挑战(我曾为此担心:他20页网上自传笔记的前5页全都是数学公式)。菲尔普斯住在纽约上东区,“在我变得非常忙之前”(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会乘坐M4公车穿过第110街,然后向北到达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所以,实际上,位于哥伦比亚大学以南30个街区的Isabella's完全偏离了这条路线。“这不在我公车路线之上,”他笑道,“但我是个爱冒险的人。我经常到公车路线以外的地方。”从传统上讲,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认可的是几十年前完成的、但今天仍适用的成果。菲尔普斯获奖,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末取得的成果,它颠覆了当时认为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传统观念——从而挑战了这样一种想法:政治家们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失业和物价上涨。但菲尔普斯还因其对欧洲大陆“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批判而著名,他认为这种“社团主义”妨碍了创业者和金融家之间的互动,导致欧洲依赖从美国进口的观念和技术。这就是他对欧洲大陆过去10年增长不尽人意的解释。
自2001年起,菲尔普斯开始担任资本主义和社会中心(Center on Capitalism and Society)主任,总部设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个经济论坛,探讨是什么促使商业想法可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中开花结果。
女服务员回来给我们点菜。我们俩都选了玉米浓汤作为头菜。然后,他选了自己经常点的马里兰蟹饼三明治。我则听从他的建议,选了一款科布沙拉,这是一款混合了鸡肉和羊乳干酪的菜品。女服务员称:“科布沙拉里有很多东西。”菲尔普斯告诉我,这种东西是在曼哈顿发明的,不过后来的研究显示它源自于加利福尼亚。
菲尔普斯觉得,他目前所处的事业阶段“让我可以想怎么激进,就怎么激进。因此我现在有很多关于资本主义的有趣想法,而且在尝试设想怎样重写经济学,才能抓住这个体系的核心。”他解释道,传统经济学将世界视为一个管道系统。“它根本上植根于均衡思想——事情按照人们期望的那样运作。”然而,资本主义现实“却是一个无序体系。创业者只拥有关于未来最模糊的图景,他们对此下注;同时还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他们不知道当他们撬动这根或那根杠杆时,会出现他们想象中的结果——这就是结果不可预知的法则。这不会出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而我职业生涯后期的任务,就是将它们写入教科书。”
那款奶白色的汤上桌了,我将话题转向了欧洲,菲尔普斯认为欧洲注定总是跟在美国后面;再者,缺乏创新使工作索然无味,难以令人满足。“我不羡慕欧洲等着看在美国发生了什么,然后再花费资源去采纳这种或那种新型商品或技术,”他表示,“我只是认为,欧洲人坚持着一种我称之为社团主义的无效僵化体系,从而剥夺了自己成为高就业经济体的机会,丧失了在工作场所激励智力创新的机会,同时也制约了个人发展。”
菲尔普斯表示,一些意大利朋友告诉他,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我们现在确实很像美国”。但尽管欧洲近来重新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但他还是看到了太多的倒退。“例如,在德国许多公司邀请工会代表就职于监事会,并就投资决策提供建议——这很难说是纯粹的资本主义。”
“当然,德国公司找到了一条出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吗?他们开始贿赂工会领袖,使其与他们站在一起——(看看)大众汽车(Volkswagen)丑闻……他们必须行贿的事实,为某些人提供了隐蔽的机会,这些人说,‘噢,这没关系,这些工会没什么力量,这只不过是在做秀'。好吧,如果这都是在做秀,那工会领袖怎么会得到如此高额的薪金呢?”
他承认,与美国进行比较,必须将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考虑在内,资本市场、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市场的兴起可能在迫使欧洲大陆发生改变。但他指出,德国重要的风险资本家都是美国人。“或许这有助于说明,在老套的州地方银行(Landesbanken,该国的公共银行)和所有那些老化、庞大的投资银行体系下,运营德国业务是多么吃力。现在德国人正从全球化的某些良好特征中受益。”
我们开始吃主菜了——我的沙拉装了满满一大盘,他则试图在一块蟹饼和圆面包上建一座塔。我想知道,欧洲有没有一点儿让他欣赏的地方呢?他又一次大笑起来。他说,还有一个人问过他这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前任财长、后来的前哈佛大学(Harvard)校长拉里•萨莫斯(Larry Summers)。“我觉得这很奇怪。这暗示着我不喜欢欧洲的任何东西……(实际上)欧洲的许多东西我都喜欢。我经常去欧洲,我必须喜欢那里。”他举了一个例子,欧洲“对哲学的兴趣比美国浓厚得多,我对此非常欣赏”。
菲尔普斯急于表明,他“不是”说欧洲人反对创造财富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我的天,我想再没有人比欧洲人更喜欢积累财富了。我曾经和妻子住在(罗马)法尼榭宫(Palazzo Farnese)附近。在杜维嘉大学(University Tor Vergata)上了一整天班后,开着我的宝马(BMW)回家,花30分钟找个停车的地方,一直到晚上6点50左右,搞得筋疲力尽。有一些意大利工匠从早上8点就开始工作个不停。欧洲人在许多方面跟美国人很像。他们喜欢工作,他们喜欢富裕。但他们的其它态度妨碍了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
在吃完主菜后,我们俩都停顿了下来。这些蟹饼怎么样,我问道?“哦,非常好,”他说,“一点也没变,一直都是这个味儿。”
他在资本主义和推行变革的必要性方面迥异的观点是不是有可能与他出生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有关?——在此期间他的父母都失业了(他的父亲从事广告工作,他的母亲是一位营养学家)。菲尔普斯加强了语气。“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的思想根本没有成型。”他跟我谈起获得诺贝尔奖后,有一次在瑞典电视台接受采访的经历:“采访者非常希望我说,我之所以进入经济学领域,原因是受到了大萧条时期失业的严重影响。我很难让他明白,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
菲尔普斯解释说,对他更重要的是上世纪50年代早期在阿默斯特学院的时光,当时他阅读希腊英雄史诗、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Don Quixote)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关于自强的书。“我想不知不觉中,我就被灌输了生机论的思想(关于什么使生命有意义的思想)。美好生活是由接受挑战、解决问题、发现、个人发展和个人变化组成的。”他读过哲学家戴维•休姆(David Hume)的书,这使他明白了“想象力在理解事物方面的重要性”,而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则提倡自由意志,反对决定主义。
相比之下,Isabella's的甜点单令菲尔普斯感到困惑。这“很奇怪,”他承认。不过,尽管他说欧洲人抵制创新,但并未挑剔酪饼冰激凌或者草莓奶油冰激凌背后的思想。“我保守一点吧,来个卡布奇诺奶油布蕾,”他说道(我不知道法国大厨是否会认为这是道保守的菜)。我选的是“黑巧克力袋”——一个大巧克力架,里面填充了奶油、覆盆子慕斯和夏季水果。
菲尔普斯回忆说,他在学术生涯中相对较晚的时期才开始从事基本工作——35岁左右。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由于10年前发表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奖。“早年的时候,我花了大量时间撰写发展经济学论文,我现在真希望当初没花那么多功夫写那些东西。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成熟起来,说出一些有创意的东西。”
我付了餐费,但当我们离开餐馆时,费尔普斯想散一会儿步。犹豫了一下,他问我是否愿意向北走一段,走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中央公园外,前面立着一个粉红色的纪念石碑,上面刻着自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姓名。纪念碑的第二面底部刻着费尔普斯的名字,是几天前新加上去的。费尔普斯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指着一些同样列在纪念碑上的同代人。他显然非常自豪。
拉尔夫•阿特金斯是英国《金融时报》法兰克福分社社长
Isabella's餐厅,纽约哥伦布大道
玉米浓汤2份
蟹饼三明治 1份
科布沙拉 1份
焦糖卡布奇诺 1份
黑巧克力袋 1份
加州白葡萄酒 2杯
双倍意式浓缩咖啡 2杯
水 1瓶
总价:100.25美元